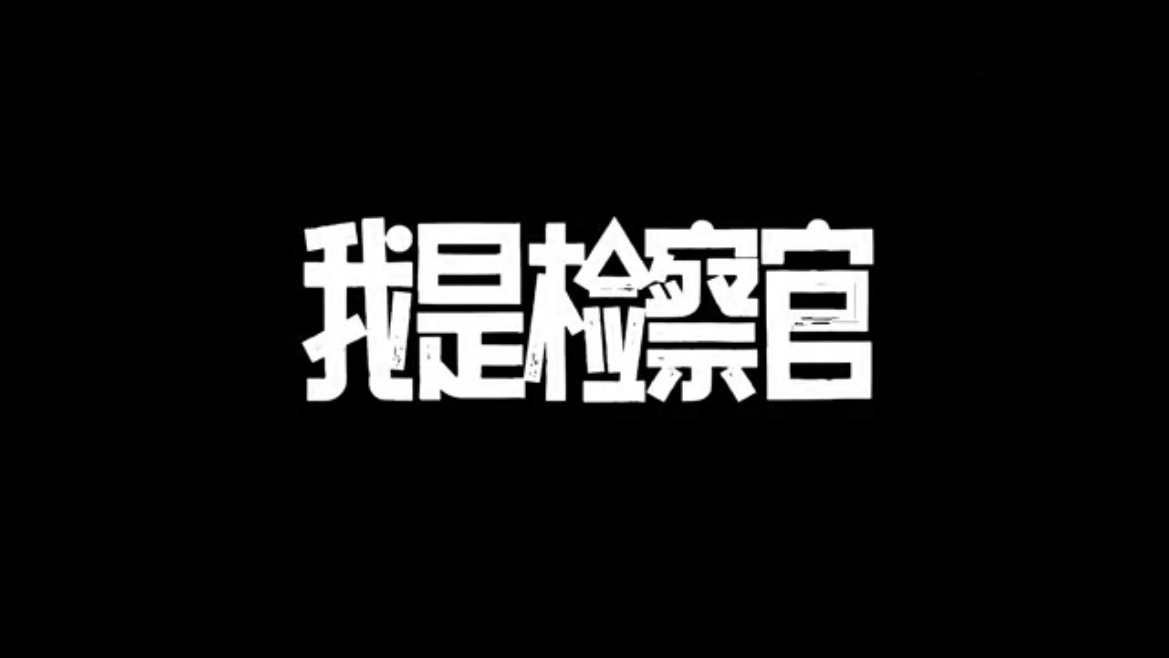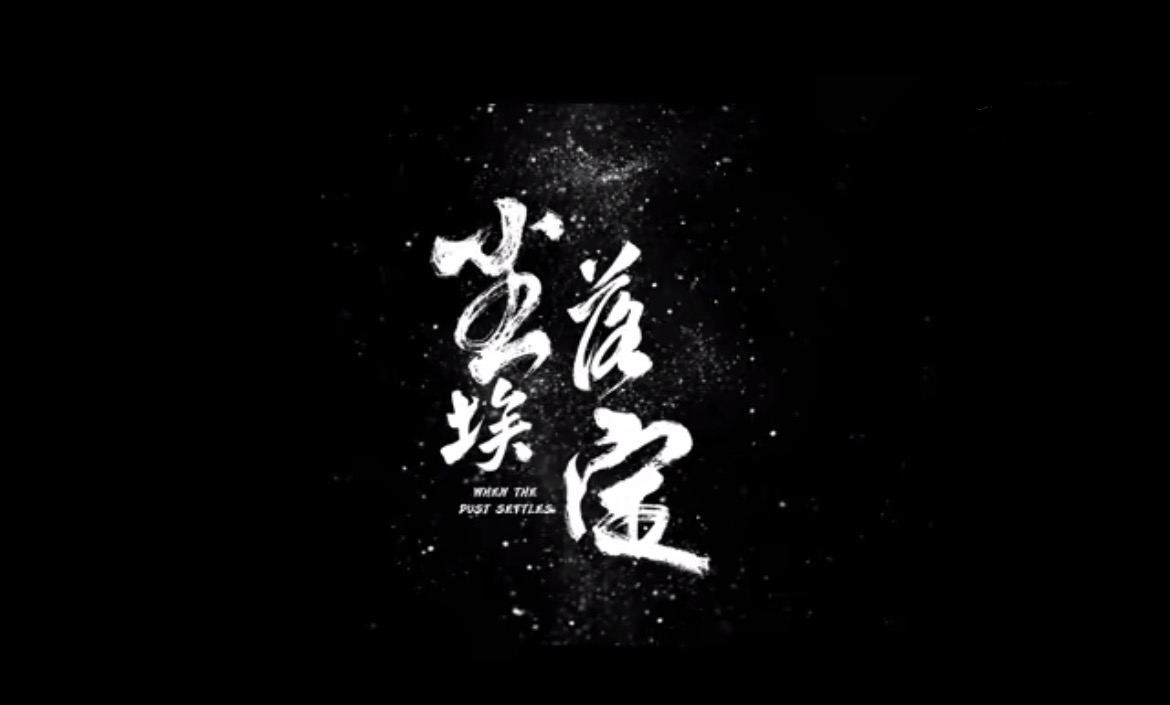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在农村的孩子,自小虽未有过断粮的挨饿体会,但对物质匮乏日子的记忆却很深刻。过去岁月,吃撑的机会或许有,但真正吃饱到不想吃的时候却少,即便米饭可以吃得饱,但过不了多久,肚子似乎又瘪了。
印象深刻的是吃番薯丝饭。那时家里人多,早上煮好的一甑饭,要吃一整天,但往往到晚上,就不够吃了。怎么办?妈妈的办法就是往白米饭里加番薯丝,余的饭多,加的番薯丝就少;余的饭少,加的番薯丝就多,反正番薯丝是够吃的,而白米饭却有限。对于番薯吃得厌烦,而米饭吃不够的我们,就会耍滑,在装饭的时候,尽量将番薯丝挑开,专选米饭装。可挑来挑去,还是番薯丝多,米饭少。遇着歉收年景,可就不是一餐晚饭吃番薯丝饭,那是大半年,一日三餐都是番薯丝饭。小孩子吃得艰难,爸妈一边对我们进行鼓励,一边心里也不是滋味。还有是遇着晚饭实在不够,邻居间会互相借饭。特别是谁家突然来客了,一天的饭往往是算着煮的,有时候邻居有剩的饭可以借,有时邻居也不够,但往往自家省着吃,将饭借给别人。为感谢邻居“危难”之助,也或表示客气大方,第二天“还饭”时会拿比头晚借饭时更大的碗,碗里盛的饭也尽量往结实里压。
吃不够,吃不好,最盼望的是过年,过年会杀猪,可以吃到解馋的鱼肉。那时,家里一头猪从年头养到年尾,杀了卖掉,自家会留一丁点猪头猪脑,大年三十夜吃年夜饭时,妈会将这些猪肉炒好,做成“丰盛”可口的菜肴端上桌,让全家大小一饱口福。但也只有一两餐,而且还不能放开吃,年一过就会收起来,不再轻易吃得着。
再有享口福的时候,那是过年请客吃饭的时候,会有切得很大喷香喷香的腊肉摆上桌,懂事的小孩知道这是用来待客的,不是炒给自己的,不能吃,只有眼睁睁看着。饭吃完,客人下席了,把肉端进厨房后,妈会从碗底翻出一小块给小孩吃。就这样一小块腊肉,也会吃得咂嘴咂舌,让整个春节都泡在腊肉的香味里。
这是正常的一日三餐,对于吃纯净的白米饭是奢侈,吃鱼肉是奢侈,而三餐之外的辅食品,除了番薯类的自家栽种食物,其他的更是奢侈。就是过年的果子,也是传统的“三大片”,但能够吃到的日子也有限。有一件事令人感慨,那就是对水果的认知,现在再平常不过的桃杏梨李等等,那时除了在念课文的时候可以看见图画,现实生活中很少见。
认识西瓜,应是我七八岁年纪。那天,我吃了晚饭去找邻居家伙伴玩,看到他们一家人切了一个什么东西在分吃,每人手上拿着一块,外皮翠绿,里瓤鲜红,很珍惜地小口小口咬着。这时我要走开,知道不能看着人家吃东西,被邻居家大人发现,赶紧叫我进去,分切了一块给我。至于当时吃下去是什么滋味,不记得了,只晓得这是难得食品,从未见过,算是开洋荤了。长大后,才知那时吃的是西瓜。
对于橘子,我还有个甜蜜的记忆。见孩子大了,爸妈分身不开,过年过节时,就会吩咐孩子单独代表家里去外婆家走亲戚。这当中也有快乐,那即是有偷摘橘子的事情可以做。记得外婆见我们小孩子坐在家里枯燥,她又拿不出更多好吃的食物招待我们,更主要为逗我们开心,这时她就轻声轻语地对我们说:“过来,你们不要吵,摘几个橘子去!”在外婆带领下,我们才发现,隔壁人家的一棵茂盛的橘子树结满了橘子,因为相隔近,好多枝条垂落到外婆家后院里来了,外婆用一根竹竿轻轻敲几下,就落下几个,欢得我们跑过去抢着捡了抱在怀里。外婆见我们欢快了,她比我们更欢快。自此,每到中秋这个节日,知道是橘子成熟季节,再要去外婆家,想到有这件乐事可做,就有了向往的心情。
那时摘下的橘子还未完全成熟,吃起来酸涩。怕人家发现,外婆还告诉我们窍门,每次不能摘多了,少数几个就可以。
时光如流水,眨眼三四十年过去,那橘子树早已消失,外婆也是近百岁的老人家了,她不再能陪着我们做这些开心事了,但橘子酸涩的甜蜜永远滋润着味蕾,且愈回味愈甘醇。
(作者单位: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