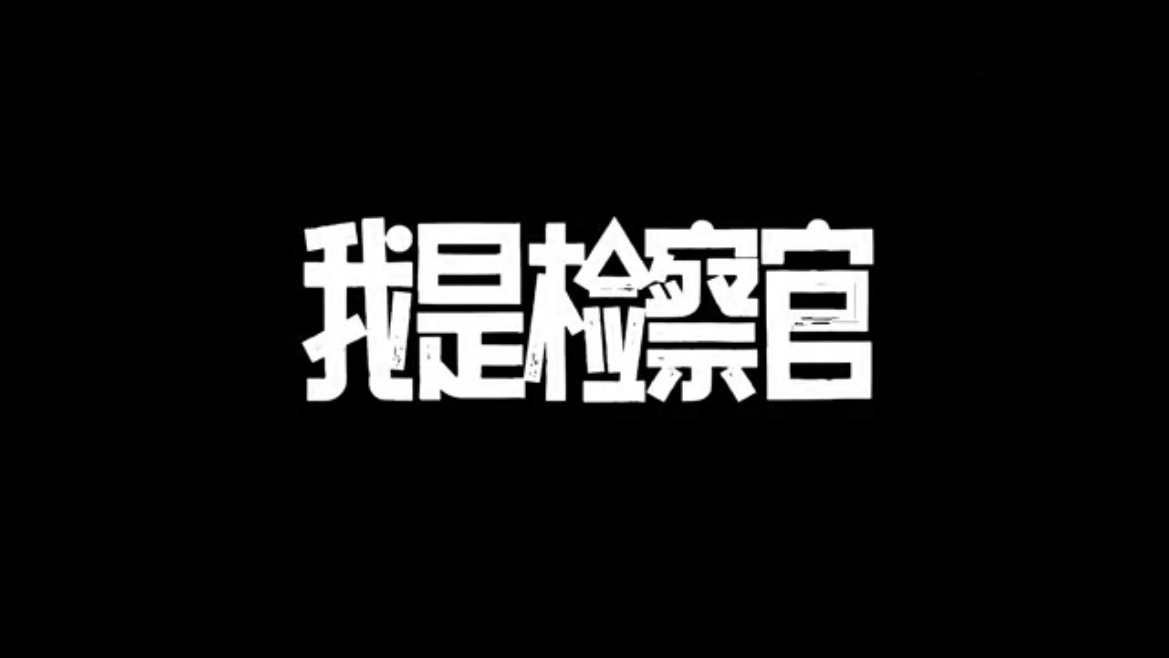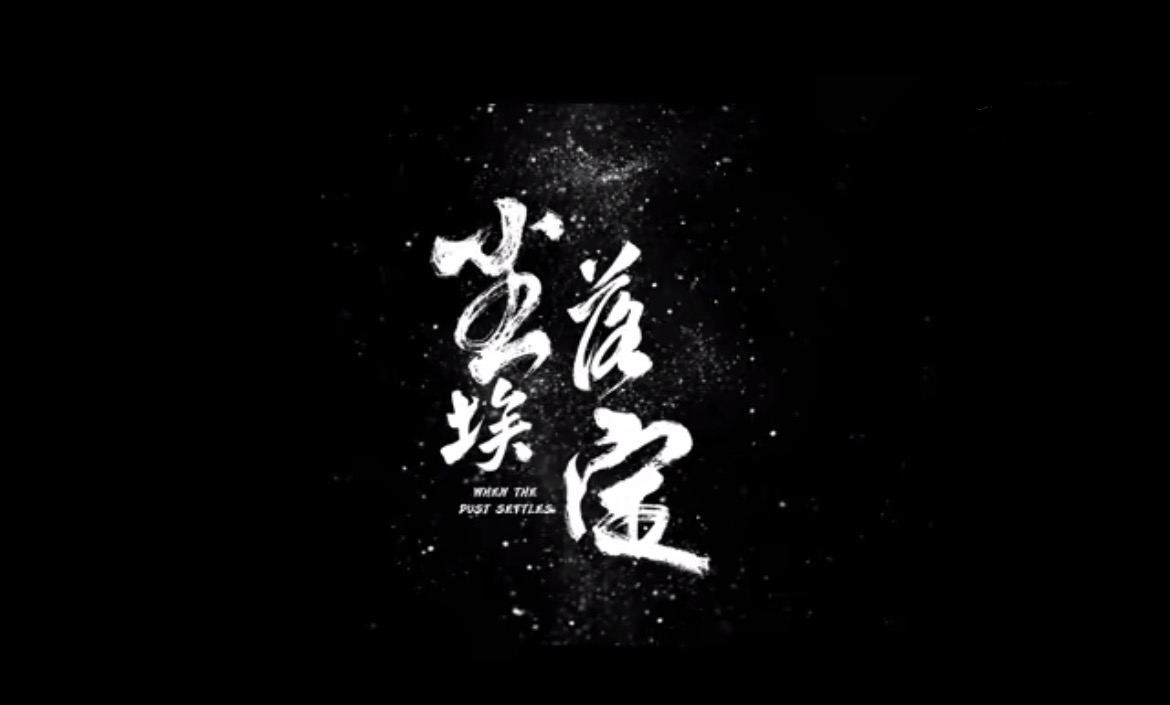◇在信息时代,各行各业特别是服务行业的职业行为,几乎都难免被犯罪实行者利用。
◇可罚的职业行为既然属于犯罪,其可罚的依据首先是具有特定的犯罪构成;其次,在共同犯罪理论的角度必然是正犯的帮助犯,所以具有帮助犯的特征;最后,其可罚的内在依据就是其为正犯的构成要件的实现提供了规范意义上的帮助。
现代社会分工呈现日益精细化的趋势,人们生产生活于与他人须臾不离的密切交往之中。在信息时代,各行各业特别是服务行业的职业行为,几乎都难免被犯罪实行者利用。例如,人们常用的聊天微信可被用于建群赌博,互联网平台可用于非法集资、销售伪劣商品,出租车可用于运送犯罪分子到达犯罪场所,快递可用于运输毒品、转移赃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显然,理论上容易给出命题:单纯被他人利用者因为缺乏主观罪过而不应接受刑罚处罚。但事实上,也有大量形式上中立、实则助益于他人实行犯罪而需要刑罚处罚的职业行为。刑法设立以中介组织人员及中介机构为主体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严重失实罪以及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帮助恐怖主义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独立罪名,目的就在于将一些典型的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或者与走私者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账号、发票、证明、许可文件,或为其提供运输、保管、仓储、邮寄等便利条件的规定“以共犯论处”,亦为处罚有关正犯的帮助犯提供了明确的指引,而这些被认定为共犯的行为,形式上大多属于中立的职业行为。
然而,现实中职业行为不胜枚举,对其类型穷尽归纳完全没有可能性,试图用规范化的刑法或司法解释将可罚的职业行为予以定型化、明确化也是徒劳之举。明智的做法,是在学理上针对职业行为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可罚判断标准或规则。
可罚职业行为的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可罚的职业行为既然属于犯罪,其可罚的依据首先是具有特定的犯罪构成;其次,既然可罚的职业行为在形式上属于中立行为、日常生产经营行为,而最终又必须接受刑罚处罚,其实质上在共同犯罪理论的角度必然是正犯的帮助犯,所以具有帮助犯的特征;最后,既然可罚的职业行为实质上以帮助犯的角色接受处罚,其可罚的内在依据就是其为正犯的构成要件的实现提供了规范意义上的帮助。结合上述三个视角,职业行为可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职业行为人对于正犯的犯罪行为及自己的职业行为可能被正犯利用,须有具体且明确的主观认识,且具有帮助正犯的意志因素。
行为人仅仅抽象地认识到自己的职业行为可能或者必然被犯罪实行者加以利用,是无须考虑帮助犯成立问题的。从客观归责的角度判断,这种抽象认识下的职业行为,虽然与正犯实行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本身没有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如果以之作为帮助犯的成立因素之一考量,势必不当压缩人们生活自由空间,人人都可能担心因某一时刻被某一犯罪利用而惶惶于心。因此,职业行为人对正犯的实行行为及自己行为可能被利用的认识,必须是当下的、具体的,自然也是明确的。当然,仅有对正犯实行行为及对自己行为可能被利用的具体认识,职业行为人也并不当然成立帮助犯。在具备认识因素的基础上,行为人的帮助故意这一意志因素对帮助犯的成立起关键作用。判断有无帮助故意的依据,是正犯实施实行行为时,职业行为人有无在认识基础上对正犯进行助益的意图。这种意图,除了分析行为人供述和辩解外,主要应立足于职业行为人与正犯当时交往的客观情状进行分析。
2.职业行为的实施对正犯实行行为起到直接加工促进作用,是当时直接推动正犯构成要件实现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可罚职业行为的直接加工促进作用,客观上辅助正犯支配犯罪实行行为往前推进。职业行为是否直接对正犯的实行行为发挥作用,重点要把握的是职业行为与实行行为在性质、方式等方面的关联程度如何?基于客观事实进行具体判断,关联程度越高,发挥作用就越直接。比如,出租车将盗窃实行者运送至某个被预定为盗窃目标的地点,出租车司机这种运输行为和实行者到达特定地点进行盗窃的实行行为直接的关联程度就极大,因为正是出租车把盗窃者拉到那个地点,盗窃的正犯才能在这个预定的地点顺利实行盗窃。但是,如果出租车司机将诈骗的正犯运往某个场所,就不能认为送客行为与诈骗实行行为直接具有较为紧密的关联,因为诈骗的实行主要有赖于实行者针对受骗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其获取财物还要取决于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此处分财产,将诈骗实行者运送到诈骗场地,无论在观念上和事实上都和诈骗实行距离太远。
需要指出,职业行为作为直接促进正犯实现构成要件不可或缺的因素,总是就具体条件而言的。也就是说,在正犯实行当时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下,职业行为成为直接助益正犯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当然,“不可或缺”不能误读为帮助行为在主体上“不可替代”。理论上有人认为,只有职业行为提供者具有不可替代性,职业行为才值得定罪处罚。比如说,假如即使出租车司机甲不提供帮助,盗窃的正犯在路边也会招呼到其他的出租车司机驾车将其运往预定地点,按照上述观点,此时甲的帮助行为是完全可以被其他人替代的,因而对甲不得认定为盗窃罪正犯的帮助犯。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任何犯罪行为、包括帮助犯,其实施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任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具体的、有条件的,而刑法惩罚的也是具体而非抽象的犯罪行为;抽离具体性和条件性,任何犯罪行为都可以被替代,因而也可以说,不得将想像的类似行为替代具体的、有条件的已然行为而免除后者的责任。
必须强调,职业行为成立帮助犯以直接加工助益正犯构成要件为前提,是就行为人正当从事职业行为而言的。如果行为人违背职业要求、超越职业范围对正犯进行帮助,其成立帮助犯则不以对正犯构成要件直接加工助益为限。例如,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车业等单位的人员,事前与犯罪分子通谋,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活动时,为其通风报信的,就成立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犯罪的帮助犯。
帮助者的不作为和实行者的作为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形
以上述两个条件判断职业行为的可罚范围,属于一般原则。由于帮助犯不仅能够以作为的形式成立,也能够以不作为的形式成立,所以必须特别讨论帮助者的不作为和实行者的作为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形。职业行为人成立不作为的帮助犯,实质上并非职业行为本身帮助正犯,而主要是在职业行为实施中行为人违反作为义务而以其不作为提供了帮助。亦即,特定职业领域或职业特殊要求条件下,行为人具有防范被正犯利用的注意义务,因未尽到注意义务而被人利用时,可能该当特定犯罪构成要件而成立帮助犯。同时,刑法考虑到特殊情况下正犯难以现实地处罚,也会把某些不作为的帮助犯独立为纯正不作为犯罪。例如,网络平台提供者未依法尽到网络信息安全监管义务的,导致淫秽物品广泛传播等严重后果的,成立纯正不作为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自己的自动缓存技术被人利用用于缓存、上传与下载淫秽视频,而仍放任不管,则同时亦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罪(有牟利目的的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实际上是以不作为的形式帮助现实难以惩处的正犯传播淫秽物品。当然,对于特定职业义务的范围应持严格解释的态度,任何特定职业义务都因其职责局限而不可能包含对所有违法情形的检视。比如,快递员只有从物品种类、外观、数量等方面检视邮寄品,具有防止违禁品、爆炸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危险物品、容易腐烂物品等国家禁止流通、寄递物品被邮寄的职责义务,但基本没有对物品质量、是否侵犯知识产权进行检视的职责义务和可能性(履行该等义务的可能性),所以,不能以快递员“应当知道”邮寄的物品“可能存在产品质量伪劣或侵犯知识产权”(抽象地认识)为由,将快递员作为有关犯罪的帮助犯认定,除非行为人明知或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非职责义务本身的要求)已经知道正犯的犯罪行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