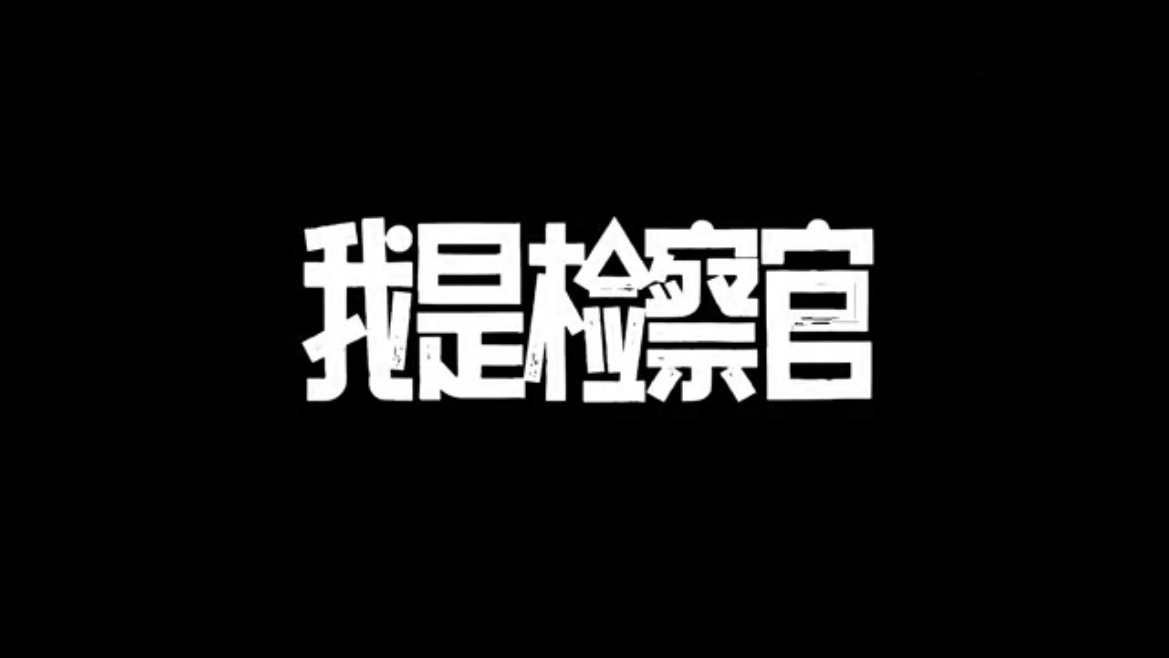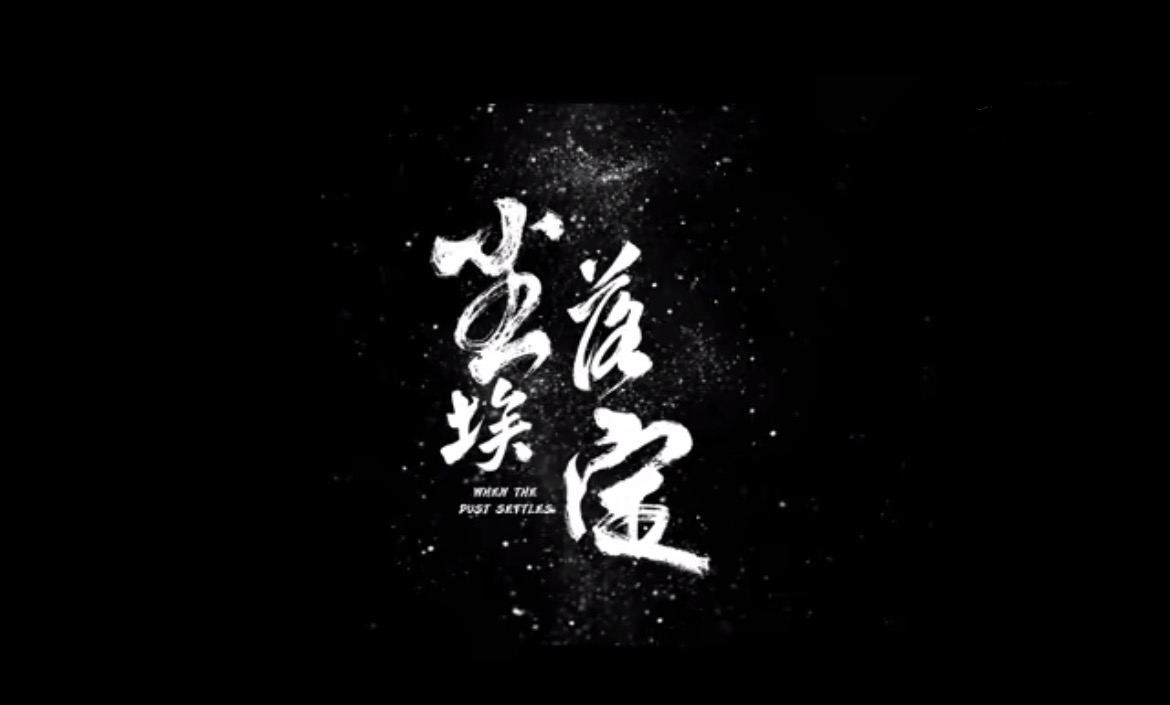1937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正是从这一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起,日本军国主义撕掉了最后的一片遮羞布,迈开了全面入侵中国的铁蹄。此前,山雨欲来之时,北平城的骚动不安早已按捺不住,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揣摩局势的走向,以及由此给自己还有自己身后的国家带来的变化。
正当人们惴惴不安时,一件大案突然降临。这年1月8日,一位早起遛鸟的北平老人发现狐狸塔下横着一具白人女尸——死者是19岁的帕梅拉。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在当时引起轰动,除了帕梅拉的外国人身份,还因为她是著名汉学家、前英国驻华领事沃纳的养女。大英帝国的雄风虽然江河日下,但英国人早就习惯在这块土地上享受特权中的特权。
《午夜北平》首先是一部关于案件侦破的著作。作者保罗法兰奇最早是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了解到这起悬案的。案发地离斯诺当时在北平的居住地非常近。正计划推出《西行漫记》的斯诺夫妇,隐约感觉正在成为一些势力攻击的对象,所以斯诺的妻子海伦坚信杀手的目标是自己,帕梅拉只是因为与自己有几分相像所以成了冤死鬼。
保罗采用了小说笔法,但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推理逻辑也极为缜密。作品并未完全局限于单纯的案件,而是将触角延伸至整个北平城,整个外侨界,甚至是国际时局——谁都知道日本挑起事端只是时间问题,但没人知道后果到底有多可怕。
案件侦破的过程扑朔迷离,仅就案件罗列的嫌疑对象而言,已经足够令人眼花缭乱:帕梅拉的养父、帕梅拉天津学校的校长、前中国男友、人力车夫……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定的作案动机,但又似乎构不成作案的关键证据。案件同时夹杂了社会民情,比如许多当地民众相信,该案是狐狸精显灵的结果。
由中英探员组成的侦破组一度非常接近案件的真相,最后之所以付诸东流,既因为探员缺乏一问究竟的努力,英使馆的傲慢,更因为英国人此时心不在焉,满脑子思索的是日军即将到来之时,大不列颠帝国如何给自己重新定位。
帕梅拉案也是洞窥当时北平混乱状况的一扇窗。保罗分析推测,帕梅拉很可能是被流落到中国的白俄贵族抛弃的婴儿。在北平三千多外国侨民中,因国内革命逃往中国的白俄人的地位最为低下。而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扬的外国人也并非铁板一块,帕梅拉被抛尸之地附近,在当时被人称之为“恶土”,充斥着罪犯、难民、醉汉、妓女、毒贩,绝大多数还是外国人。
案件引起的轰动并未持续太久,这不仅因为破案工作迟迟没有进展,还在于日军兵临城下,整座北平城人心惶惶。从保罗掌握的资料看,帕梅拉遇害当晚,目击证人众多,按理说查清真相并不困难。该案之所以被归入奇案,并非真因作案者手法有多么高明,真正的根子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字:“乱。”乱,是犯罪的天堂;乱,是怪诞的沃土;乱,也是“洋人” 不顾同胞、掩盖丑闻的遮羞布……大不列颠帝国早已抛弃了所秉持的法治理念,托辞尽显敷衍。
保罗接受媒体访问时引用了作家雷马克的话,“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但是一百万人的死亡就只是一个数字”了。在战争的洪流面前,人如蝼蚁,命似草芥。帕梅拉的遇害,只是人们遭受更大灾难的一个小小“前奏”。
帕梅拉案告诉我们,历史总会绵延不断地堆积尘埃,但尘埃之下,总会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