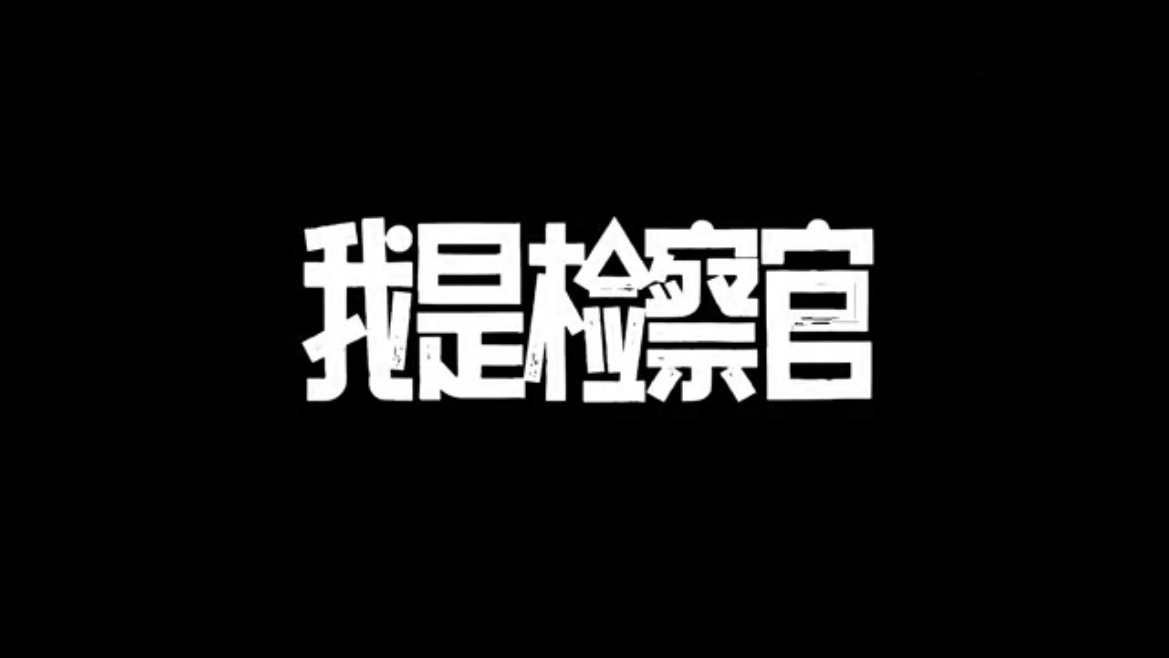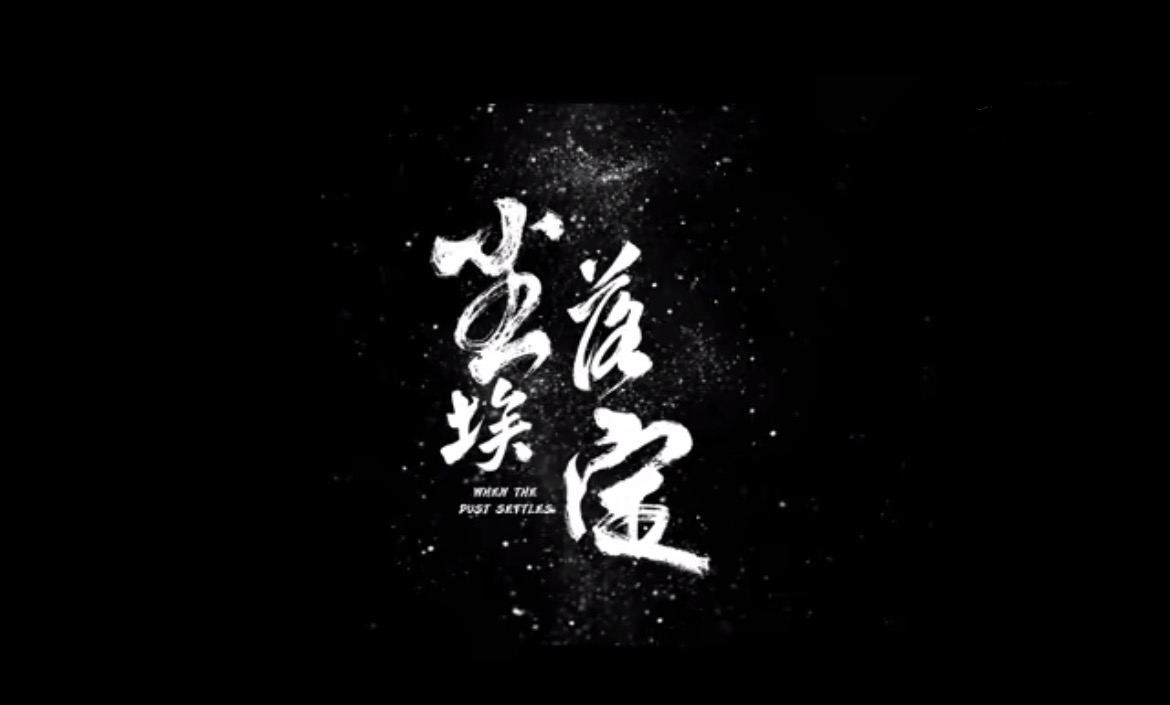杜周,字长孺,西汉南阳郡杜衍县(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他任御史时,受命查办沿边郡县因匈奴侵扰而损失的人畜、甲兵、仓廪等问题。他严格追究造成损失者的责任,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由于他执法严峻,奏事称旨,因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更为严酷。当上廷尉之后,他按照前任张汤的传统办案做法,而且比张汤更善于窥测汉武帝的心思,“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只要是汉武帝想要治罪的,他千方百计加以陷害;只要是汉武帝想宽大处理的,他也能设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之后,慢慢让案件透露出一些冤情来,以便不露形迹地从宽处理。
由于杜周在廷尉任上老是逢迎皇帝,不按照法律办事,在当时高度重视法律的社会背景下,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有人曾当面指责他说:“你为天下执掌刑律,不根据三尺竹简上写的法律条文,而专凭皇上的意旨作为治狱标准,难道可以这样办案吗?”杜周听后却不以为然,还堂而皇之地说:“三尺竹简上的法律条文是从哪里来的?以前的皇帝认为对的就可以著为法律,后来的皇帝认为可行的就不是法律了吗?什么时代有什么时代的法律,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古法可以遵循呢?”他的这番说辞只是狡辩而已。
正因为杜周善于察言观色,喜好歪曲法律来逢迎皇帝,唯君主之命是从,所以他深受汉武帝的信任,不断受到重用。在他当了廷尉之后,汉武帝改变了原来的惯例,凡是皇帝交办的案件——“诏狱”,都直接交给廷尉承办,不再像过去那样,先交给侍御史、御史中丞之类的皇帝特使专案专办,最后才交给廷尉来判刑。汉武帝打击老臣旧贵,杜周秉承他的旨意缉捕、审讯的案件也就随之越来越多。在他管理的廷尉监狱里经常关押着上百名“二千石”(地方郡守、朝廷九卿一级)以上的官员,这些人的生死全凭杜周揣测汉武帝的心思来决定。一时之间,杜周的权势炙手可热。
除此之外,再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他所在的衙门一年的案件就多达千余件。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数百人,小的也有十数人。这些原本无辜的平民,远者跋涉数千里而来,近的也有几百里。公堂对质时,官员责令证人要按官府的意向作证,稍有违反,便动刑拷掠,直到强行达到目的为止。这样一来,平民百姓一听说要被叫去作证,无不吓得东躲西藏,有的甚至十多年不敢回家。杜周在其廷尉任内,诏狱逮捕的人达六七万之多,而参与办案的执法官吏在此之外又牵连祸及十余万人。杜周执法之苛刻、手段之严酷由此可见一斑。
汉武帝时代,被认为是汉代官吏执法由“循谨”向“暴酷”的转折点。酷吏唯君主之命是从,把国家的法律视为贯彻君主个人意旨的工具。为此,他们可以不惜曲解法律,处事办案极尽苛刻之能事,尽力陷人于重罪。无怪乎司马迁的《酷吏列传》里总共写了十个人,其中之一就有“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的杜周。在书中,司马迁以鄙夷的笔法写道:“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此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